一紙鑒定推翻公證遺囑 老年群體傳承意願如何保護
近年來,隨著國民個人財富的日漸積累以及遺囑意識的逐步加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有意識地運用遺囑來對自己的財產進行身後安排。但不為大眾所知的是,在實踐中遺囑往往因各種原因,可能會在立遺囑人去世後被認定為無效,使得傳承意願無法實現又無從補救。
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在全國審理的遺囑繼承糾紛案中,遺囑被確定無效的案件超過60%。而遺囑被確認無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立遺囑人不具有完全行為能力。根據我國法律規定立遺囑人必須具備完全行為能力,遺囑方為有效。所以,老年人身故後一旦發生遺產爭議,那麼在爭議中,立遺囑人訂立遺囑時是否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便會成為首當其衝的問題。
作為深耕於家事領域的執業律師,筆者辦理了大量繼承糾紛案件,發現關於老年人訂立遺囑的意思自治自由表達的司法保護力度非常不夠,也揭示了老年群體訂立遺囑時存在一定的風險。下麵筆者將以我們代理的一個案件為例,進行具體分析(客戶和案件資訊已做保密處理)。
一、老人立公證遺囑將財產全部遺贈
侄女,法院認定遺囑無效
我的客戶古大姐,是一個非常樸素的五十多歲的女工,連律師費都是籌借的,在如此清苦的情況下,為何古大姐還要堅持起訴呢?故事還要從四十多年前說起……
當時古大姐只有13歲,還在南方老家讀書,她有一個親大伯在北京工作,已經六十多歲剛辦理了離休。古老是老革命軍人,解放後在某部委工作,和老伴生有四個兒子,但是因為夫妻感情不好已經多年分居,四個兒子也很少去看他。老爺子離休之後就很孤單,沒有人照顧,老家的親人很擔心他。1984年,古老回老家探親,和家裏親人商量後,把13歲的侄女古大姐接到北京來一起生活。來到北京後,古大姐就沒有再上學,如同親女兒一樣照顧大伯。古老對於子女對其不聞不問非常失望,將侄女視如己出,便在2009年,前往公證處訂立了公證遺囑,決定將其所有財產遺贈給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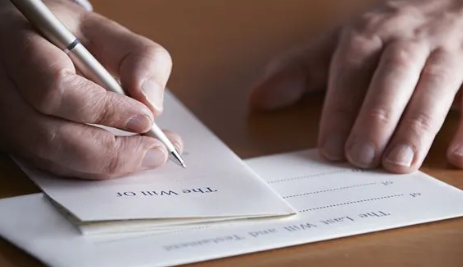
古老去世後,他的配偶和四名子女對遺囑效力提出異議,古大姐為原告,對方為被告,雙方對簿公堂。被告以古老曾經在1999年和2000年患有腦梗為由,主張其在訂立遺囑時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並申請對古老的民事行為能力進行鑒定。本案法院先後委託三家鑒定機構對古老進行已故自然人既往民事行為能力鑒定,前兩家鑒定機構均因鑒定資料不完整、不充分及鑒定要求超出鑒定機構能力為由,對該鑒定申請決定不予鑒定。一直到第三家鑒定機構,才終於接受委託,鑒定機構依據一段古老在公證機關訂立遺囑的錄影,評定古老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由於有了專業人員的鑒定意見,法院在判決時未採納公證人員在公證底檔中關於老人意識清晰、表達清楚的判斷,也沒有采信其他相反證據,僅以該鑒定意見為主要依據,認定公證遺囑無效。古老的意願和古大姐的心血全部付之東流。
對這個案子的判決,我們在看到鑒定結論時就基本預料到了結果,但是這一份鑒定意見,無論是檢材的內容,還是專業的論證,作為代理人的筆者認為均存在很大的問題。而且,從這個案子筆者還感覺到一種深刻的不安——人老了就沒有資格訂立遺囑了嗎?
二、一份過於隨意的自然人既往
民事行為能力鑒定報告
其實接受鑒定的這家機構在業內非常權威,如果筆者是法官,基於對專家的信任也會傾向采信這份報告。但是,我們詳細對比了行為能力鑒定的醫學和法學標準,並申請鑒定人員出庭接受質證,發現這個鑒定報告非常值得推敲。
首先,鑒定報告依據的檢材不夠充分,達不到認定“精神障礙”的四項醫學標準。
在本案中,判斷古老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理由在於,古老有精神障礙。根據《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的規定,確定被鑒定人是否患有精神障礙,需要被鑒定人患有腦部疾病,且該疾病滿足以下四項標準,即症狀標準、嚴重標準、病程標準和排除標準,其中症狀標準需要有軀體、神經系統及實驗室檢查證據。但在庭審中,鑒定人員明確表明本案中無神經系統檢查證據,僅是根據一段公證錄影中老人幾個回答問題存在記憶錯誤與口誤得出了古老有精神障礙的結論。但實際上,公證員問了大概170個問題,回答不清晰的有不到10個,多數問題在公證員追問後,古老也給出了正確答案。同時,在2010年的一項住院病歷中顯示,古老意識能力、定向能力等均為良好。鑒定人員在出具鑒定結論時,對於該項直接證明古老在立遺囑近1年之後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相反證據的排除適用,沒有給予充分的理由,並明確承認本次鑒定意見僅根據無法完全還原現場情況的錄影,沒有參考其他病歷資料。所以,我們認為檢材不夠充分,參考檢材無法認定 “精神障礙”達到四項醫學標準,而且鑒定人員對檢材有傾向性的取捨,無法讓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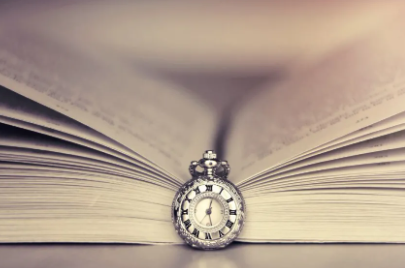
其次,該鑒定意見缺乏必要的論證,達不到認定“限民”的法學標準。
意識障礙與行為能力受限是二個概念,前者並不必然導致法律意義的行為能力瑕疵。成年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是指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在本案中,古老對於訂立遺囑、遺贈給侄女的意思表示真實清晰,對於該行為的性質與法律後果也完全理解,並符合心願。本案的爭議焦點是古老對於其民事行為(訂立遺囑)是否有清晰的認知與判斷。但在本案的檢材中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能證明古老對於訂立遺囑認識不清、無法判斷法律後果。相反,無論是古老給單位的材料、聘請律師寫遺囑、本人自願去公證處做公證,還是公證處底檔的談話記錄,都是生前完整的證據鏈,能證明他本人的意識能力足夠完整,能準確認知與判斷訂立遺囑的後果。
鑒定人員雖然是神經醫學專家,但在做出鑒定時不光要考慮醫學鑒定標準(即使醫學標準,本案鑒定也不符合),還要達到法學標準,即充分論證當事人意識障礙的程度達到了“不能完全判斷自己行為”。而本案鑒定人員關於是否達到法學標準完全一帶而過,沒有充分論證古老的智力與精神狀況不能理解和判斷其將財產遺贈給侄女的行為性質與後果。而更多的證據顯示,古老本人對該行為具有完全的判斷能力。
最後,身後鑒定無法準確回饋訂立遺囑時的真實場景。
本案中,公證人員曾與古老進行了二個小時的現場筆錄,對其做出了雖然反應稍緩,但是表達清晰,意識清楚的判斷(見公證底檔)。而鑒定人員依據的錄影只是事後觀看,無法直接還原當時的場景,資訊存在一定衰減。而且,鑒定人員認為古老回答問題有誤,從而認定存在記憶障礙、定向障礙。但是僅憑一段對話,是無法排除由於被鑒定人年齡、學歷、法學知識、公證人員提問方式對其回答問題準確性的影響。筆者認為對於已故自然人行為能力鑒定本身就要非常慎重,因為它無法還原當時情景,無法對活體自然人進行鑒定,其次還存在超出鑒定機構鑒定能力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前兩家機構都拒絕進行鑒定的原因。
綜上,如果對於一份鑒定內容和過程有瑕疵的結論,僅因出具人是專門鑒定機構就確認其不可置疑的證據效力,而不顧其他相反證據,那麼未來年邁的老年群體所訂立遺囑的效力,就完全掌握在鑒定專家手裏,遺囑的效力將充滿不確定性,這是最危險的。
三、本案引人深思的是關於行為能力
認定的“唯鑒定論”
本案中,立遺囑人即便選擇了最為穩妥和嚴謹的方式訂立遺囑,其傳承意願最後也未被法院所認可,引發了筆者對類似案例更深一步的思考。
1.遺囑繼承中老年人面臨的意願表達困境
據上海長寧法院發佈的《2017 年-2020年涉遺囑繼承糾紛審判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數據顯示,立遺囑人年齡在60周歲以上的案件有 449 件,占比 81.93%,可見訂立遺囑的被繼承人普遍高齡,而心腦血管疾病在高齡群體中是極為常見的,萬一病情嚴重,導致老人口齒不清、行動遲緩,那麼他們立下的遺囑是否都存在後續被推翻的可能性,這種情況下老人表達傳承意願的自由該如何得到切實的保障與落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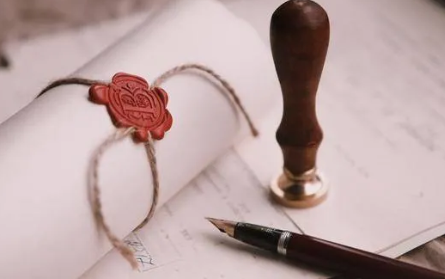
由於遺囑是死因行為,即以被繼承人死亡為生效要件,這就導致不可能通過詢問被繼承人來確認遺囑的真實性和真實意思表示,因此,在司法實踐中也就只能要求訴爭雙方各自舉證。那麼若被繼承人患有腦梗等比較影響反應快慢的疾病時,繼承人對被繼承人訂立遺囑時的行為能力提出質疑,舉證責任該如何分配?法院應該用什麼樣的標準去認定被繼承人訂立遺囑的效力?是否僅依據一個鑒定意見便足以得出結論?反過來再問,如果本案中被繼承人未訂立公證遺囑,只訂立了合法有效的自書遺囑,在沒有公證錄音錄影的情況下,該遺囑也會面臨被推翻的問題嗎?如果不會,僅通過鑒定來判斷遺囑效力的認定是否過於不公平?
不過上述的一系列問題,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都尚未得到有效的解決……
2.遺囑效力認定應當充分保護立遺囑人的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也是民法的基石。在繼承法中集中表現為遺囑自由,遺囑人享有依其意思表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對自己的事務進行最後的安排與管理的權利。
遺囑體現的是遺囑人對其一生奮鬥所得的回顧、審視與安排,是意思自治原則在繼承法中的直接體現,承載著民法對於個人選擇與意願的尊重與保障,這也是其效力比法定繼承更為優先的法理基礎。因此,筆者認為,法院審理遺囑效力糾紛之時,否定遺囑效力時需持更為嚴謹和審慎的態度,以期更好地保障並激勵公民對私有財產的自主決定權。對於明顯有瑕疵的鑒定報告,應該給當事人重新鑒定的機會。在本案中,由於沒有其他鑒定機構接受委託,意味著這家機構的鑒定報告得不到其他機構的檢視,以此為據剝奪了當事人救濟的可能性。
3.“唯鑒定論”的危險:如鑒定報告有誤,缺乏必要的救濟途徑
對於已故被繼承人,因其所立遺囑的效力直接影響繼承人的合法權益,故法官對其行為能力是否存在瑕疵進行判斷時也是格外嚴格的,一般都會以客觀判斷依據為主、以主觀判斷依據為輔、主客觀依據相統一,以達到證明標準。
為了最大限度查明遺囑意願的真實性,法院在認定遺囑人訂立遺囑時的民事行為能力時,要綜合全案證據,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的規則,即鑒定意見、門診病歷等客觀證據中關於精神狀態行為能力的表述要和當事人自述保持一致,形成環環相扣、相互印證的完整可用的證據鏈,以達到民事訴訟中“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因此,鑒定意見因其具有專業性、合法性、確定性的特點對法官的判斷產生較大影響也無可厚非。

筆者並不否認鑒定意見的重要性,但是現在的問題在於,鑒定意見本身可能並不準確,並缺乏相應的復核和審查機制,對鑒定意見有異議的當事人也很難取得快速有效的救濟途徑,導致在一個遺囑繼承糾紛案件中,鑒定意見的做出基本就決定了案情的整體走向,這也就是筆者認為“唯鑒定論”的不合理之處。法官在做判斷時還是應該更為客觀地看待鑒定意見的證明力,而不是過分依賴,要跳出所謂專業結論的桎梏,從更多的方面去衡量和考察案件本身的立法思維與法律邏輯。
比如回歸本案,被繼承人是否具備民事行為能力這一問題,除了鑒定意見外,我們作為代理人提交了多份證明被鑒定人對遺贈行為具有完全理解與判斷能力,清晰認知法律後果的證據,可惜法官並沒有采信,而是內心心證認為鑒定報告更有專業性。這就面臨了一個危險境地——如果鑒定結論出錯呢?
在本案中,我們曾經要求針對該鑒定報告請示業務主管單位,詢問對於已故自然人既往行為能力是否可以進行鑒定,鑒定的法定檢材和標準是什麼,但是被法官拒絕了。司法實踐中,目前也沒有明確的對於鑒定報告提出異議的救濟途徑以及鑒定結論準確性的核查機制。實際情況就是,司法鑒定結論一旦作出就很難被推翻,當事人如果存在異議,重新鑒定的申請要得到法院的批准,需要承擔較大的舉證責任,當事人幾乎無法尋求到其他的救濟措施。
四、律師建議
隨著我國老齡化問題逐步凸顯,訂立遺囑日漸成為老人自由處分財產、傳承家庭財富的重要手段。然而由於老百姓對繼承相關法律認識的不夠,以及目前的司法實踐,導致遺囑最終的效力認定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因此,作為多年深耕家事領域的律師,薛京律師在此提出以下建議:
1.儘早規劃遺囑安排,諮詢專業人士進行指導
為了避免遺囑人被認定在訂立遺囑時欠缺民事行為能力,我們建議遺囑人早做規劃,在確定自己理想的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之後儘快諮詢專業人士,在專業人士的幫助下,生前主動進行民事行為能力鑒定、起草符合法定形式的遺囑,如自書遺囑、公證遺囑等。不要等到醫院積累一大堆腦梗等腦部疾病病歷,再去做遺囑。
2.多工具進行財富傳承規劃,避免單一遺囑被認定無效
由於遺囑存在事後被認定無效的風險,我們建議採取多種傳承工具組合的方式對複雜財產進行安排。如在專業律師的幫助下將大額保單、家族信託等更為靈活的工具納入自己的規劃範圍,更好地實現自己的真實想法,不要將所有的財產都放進一紙遺囑,以免傳承意願因為未知的情形而落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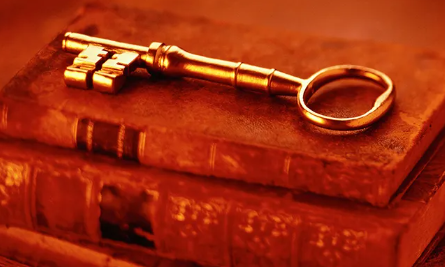
3.如已經產生糾紛,建議多方收集證據,還原立遺囑人真實意思表示
被繼承人之所以訂立遺囑,是因為不希望繼承人之間因遺產繼承爭議不斷,不利於家庭親情的維繫。但是如果真的產生糾紛,也不必一味逃避,繼承人應最大程度地收集證據,還原被繼承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比如錄音、錄影、醫療機構醫生和公證處工作人員等專業人士的證人證言,與被繼承人接觸最為頻繁和直接的左鄰右舍所提供的證人證言等,來準確認定被繼承人的真實意願。
總之,這個案子不是法律技術的較量,而是對老年人意思自治困境的漠視。我們做了所有的工作,但是在一份輕慢的鑒定結論前顯得以卵擊石。這個案子給我們的啟示是,一是要重視老年人訂立遺囑的尊嚴與權利,對於與繼承及遺囑效力相關的行為能力鑒定要有更加嚴格的醫學與法學標準;二是,訂立遺囑要趁早,否則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不知不覺間喪失了通過遺囑保護我們愛的人的權利。
免責聲明:本平臺不保證所提供資訊的精確性和完整性,內容僅供學習交流和參考,對任何人使用本資訊所引發的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失均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我們旨在傳播美好。
本平臺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若平臺發佈的內容涉及侵權或來源標記有誤,煩請告知,我們將根據要求更正或刪除有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