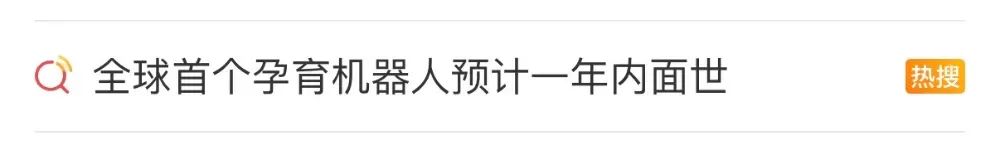近日,一條名為“全球首個孕育機器人預計一年內面世”的話題登上熱搜第一。該消息稱,國內某機器人公司創始人正在打造全球首個孕育機器人。該系統能模擬子宮環境,並整合到仿人類機器人體內,讓“機器人媽媽”完整復刻從懷孕到分娩的人類孕育全流程。預計“樣機”將在一年內推出,並且定價計劃控制在 10 萬元內。難道“人造子宮”馬上就要問世了?
植物的種子扔水裏就能發芽,受精的蛋用恒溫箱也能孵化。而科技發展至今,包括人類在內的哺乳動物們卻仍然不能脫離母體,以純人工的方式從頭孕育一個生命,為什麽?
撇開費用問題和倫理道德的爭議不談,即便從純技術層面討論,人造子宮眼下也還有太多的技術難題無法解決。
如果你也關心人造子宮的研發進展,但不了解具體的進程,就來看看本文。相信看完之後,你也能和該領域的研究人員一樣,一樣的一籌莫展。
受精卵經過數天的卵裂,變成含有囊泡結構的胚泡後,就必須植入分泌期的子宮內膜,和母體的子宮建立血液交流。這一過程稱為“著床”。
著床意味著早期胚胎開始從母體的血液中獲得氧氣、營養、免疫等全方位的支持。此後,早期胚胎繼續發育出胎盤,作為母親和胎兒之間傳遞物質的樞紐。胎盤把媽媽血液中的養分匯聚過來,通過臍帶的靜脈輸送給寶寶,再把寶寶從臍帶的動脈送出的代謝廢物過濾給媽媽帶走。這便是寶寶從一個早期胚胎發育成足月成熟胎兒的主要過程。
圖庫版權圖片,轉載使用可能引發版權糾紛
這個過程極為依賴母體。所以,臨床上如果有胎盤、臍帶血流不暢的情況,很容易導致胎兒發育異常;如果有各種原因造成胎盤、臍帶的血流阻斷,數分鐘內就可導致胎兒死於宮內。那麽,既然胎兒的發育離不開胎盤這個“樞紐”和臍帶這個“傳送帶”,只要制造一個人工母體代替媽媽的子宮,和胎盤進行血液交換,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事實上,胎盤並不是簡單地依附在子宮內膜上,而是與母體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適應機制。除了物質交換的功能外,胎盤還分泌激素和多種生物活性物質,向母體釋放信號使其發生適應性改變。女性懷孕後血液稀釋,凝血功能和血流動力學發生改變,免疫系統也能耐受明明是“異物”的胚胎,這些改變都和胎盤的調控有關,也都指向同一個目標:讓胎兒獲得當下最合適的發育條件。這就為人工母體的開發帶來了第一個難題:胚胎發育的過程中,每時每刻的需求都不一樣,人造的母體很難像真正的母體那樣,對胎盤釋放出的信號作出及時的反應和精細的調整。為胎盤提供最合適的血流灌註壓力、氧分壓、營養物質濃度,更不用說提供免疫因子等復雜的生物活性物質了。而更麻煩的問題是,胎盤很難在脫離母體的環境下長期存活。早在 1967 年,Panigel 和他的團隊就開始嘗試胎盤的體外灌註。五十余年來,無數人相繼進行類似的嘗試,但即便是第一時間取得的新鮮、完整的胎盤,離體十余分鐘便可產生微血管血栓,顯著降低灌註成功率。大多數研究也只進行了數小時的灌註實驗,胎盤灌註時間不超過 48 小時。雖然 Polliotti 等人證明了多日灌註具備可行性,但幾天的時間窗相較於維持一個胎兒的完整發育所需要的時間來說還是太短了。且因為胎盤灌註系統的復雜性,即使是經驗豐富的研究人員,單次灌註的成功率仍然很低[1]。除此之外,胎盤長期處於 37℃ 的外部環境下,如何防止感染也是一大難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全部解決,用人工母體從頭孕育生命的設想就不可能實現。而其中的很多細節以當前的醫療水平來看,都是難以逾越的高山。話說到這裏,有些讀者朋友可能會疑惑:以前不是有過“人造子宮研發成功”的新聞嗎?他們是怎麽克服這些難題的呢?其實,那些新聞中的人造子宮並沒有克服這些難題,它們並不能從頭開始孕育胚胎,但那些實驗的成功仍然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臨床上時常有孕婦意外地提前娩出健康的胎兒。有時候,孕婦自身的健康問題也可能迫使她們不得不提前終止妊娠,以免病情發展下去危及自身生命安全。如果是胎齡已接近足月的早產兒,雖然仍可因為各器官發育不夠成熟出現呼吸窘迫等問題,但大多都能在新生兒科的照護之下存活下來、健康長大。而那些月份過小的胚胎,往往在脫離母體的時刻便已失去生機,雖然令人惋惜但以眼下的醫療條件也無可奈何。最令人痛心的是那些中期妊娠時娩出的健康的極早產兒。明明器官已經基本成形,只待進一步發育成熟就是一個健康的寶寶,可由於出生過早,身體的各器官都無法支持他們獨立生存,人們只能眼看著那些瘦弱的寶寶慢慢失去生命。眼下雖然有多種生命支持方法可以試著幫助極早產的寶寶存活下來,但很多重要器官必須在羊水環境中才能發育完善。比如說:極早產兒的肺泡和毛細血管如果提前接觸空氣,會擾亂正常的肺泡發育,導致呼吸衰竭。極早產兒的胃腸道未發育完善,直接餵養可導致餵養不耐受和壞死性小腸結腸炎,而如果只在靜脈輸註營養液又會因為腸內餵養不足會導致腸道萎縮、細菌易位和敗血癥。寶寶在母體中吞咽羊水,說明羊水中的某些營養和活性物質可能是胃腸道發育完善的關鍵。羊水環境還能預防肢體粘連及相關畸形。所以,一些極早產兒雖然能救治成功,但很容易因為先天不足留下重大的健康隱患,嚴重影響未來的生存質量。在此情形下,人們當然會想到:如果可以模擬出宮內的生存環境,讓極早產的寶寶再多發育一段時間,豈不比任何補救措施都有效?但正如前文所言,精確的母體環境和無法離體生存的胎盤是解決不了的難題。多個國家的醫療團隊都嘗試過在動物實驗中研發人工胎盤,可感染、臍血管痙攣、血管壓力無法精準匹配等問題總是讓早產的動物胎兒短期存活後便死於各種技術缺陷,直到 2017 年,美國費城兒童醫院的實驗繞開“人工胎盤”這個技術難點另辟蹊徑,讓相當於 23-24 周人類胎兒大小的羔羊寶寶們在離開母體的環境下生存了 670 小時(約 28 天),才讓人們看到了人造子宮造福早產兒的新希望。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費城兒童醫院開發的這個人造子宮需要依賴早產兒自帶的臍帶建立新的循環系統,所以它只能幫助早產兒進一步發育,並不能從零開始完成整個孕育胎兒的過程。且由於法律法規、道德倫理、醫學可行性、遠期健康風險等多種顧慮,這項技術距離全面應用到人類寶寶身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那麽看到這裏,你體會到相關專業人士的無奈了嗎?
不過,即便有這麽多難題懸而未決,我依然驚喜地看到新聞報道有人聲稱能在一年內開發出復刻人類懷孕到分娩全流程的“孕育機器人”,或許他們手中掌握了人類醫學界尚未知曉的先進技術吧!真令人期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