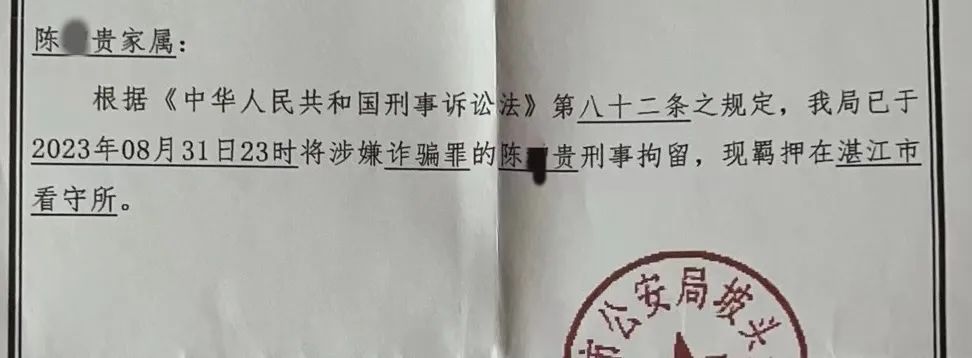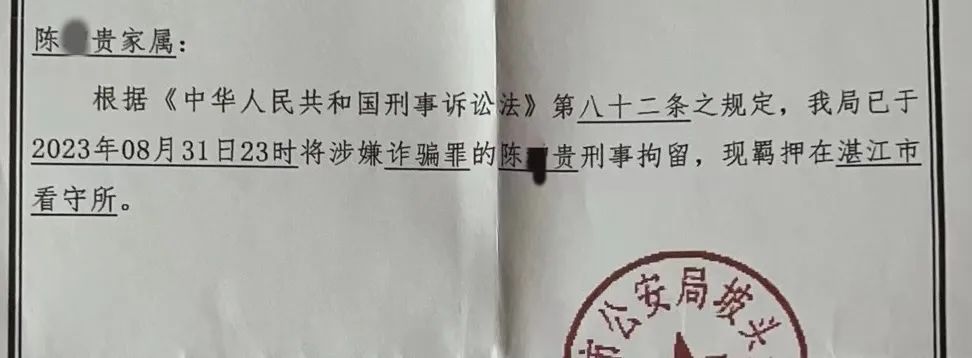近日,有人因為“做法事”而被控詐騙,一時引起討論。檢方指控稱,陳一、陳二從事封建迷信活動,並通過虛構做法事為逝者招魂超度而騙取他人財物共計86800元。庭審中,“做法事為逝者招魂、超度”與“不做法事會使逝者魂不附體、影響子孫”等是否屬於詐騙罪中的“虛構事實”,成為控辯雙方論證的焦點。而新聞采訪也曝出,被控的陳一、陳二祖上幾代都從事“做法事”的行當,陳一更是已逾40多年。我和自己帶的刑法學研究生討論了這個案件。最初大家都義憤填膺,認為這怎麽可能會是犯罪,如果這是犯罪,那麽很多寺廟裏的香火錢不都構成詐騙嗎?李四夫妻關系不睦,於是找張三真人算命,張真人掐指一算,大呼不好,你老公被狐貍精勾引了。需要造一座寶塔,鎮壓狐妖,大概需要250萬。李四最不缺的就是錢,直接給了張真人一張250萬的支票。寶塔造好之後,張真人對李四說:“現在你們的夫妻感情一定會牢固得不得了。”這個時候,寶塔忽然劇烈搖動,張真人大呼不好,這個狐妖敢情是千年白狐,還要追加250萬,造一座比雷峰塔都堅固的鎮妖塔,李四又給了250萬的支票。但是兩個250萬還是無法避免老公被狐貍精勾引的事實,兩個月後李四的老公出軌了新的女秘書,李四氣壞了,把張真人告了。
張三已經連續失戀三次、失業四次,心煩意亂,正好在天橋上遇到算命先生李四。李四見張三瞅了他幾眼,於是對張三說:“先生你好,有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張三最後只能通過小額貸款平臺,貸出1萬塊,從李四處獲得了天機。天機就是買一只野狗,殺了後把狗血在身上一潑,血光之災就解了,但可能還會有桃花劫,如果要解桃花劫,還要再花一萬。張三說桃花劫就不用解了,自己隨機應變即可。
張三沒有考上公務員,所以跳樓自殺。父母非常難過,找到張大仙幫其超度。張大仙知道張三生平最大的願望就是考上公務員,所以對張三的父母說:“如果花1萬塊錢,可以做一個特殊的超度儀式,感動太白星君,他是天上管公務員考試的,弼馬溫也是他任命的。所以來世張三一定能考上公務員。”
討論了這三個案件之後,同學們混亂了,覺得剛才還知道什麽叫做詐騙罪,現在已經完全不知道什麽叫做詐騙罪。
我國刑法對詐騙罪的規定非常簡單,何謂詐騙?詐騙就是詐騙,“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就構成犯罪,根據司法解釋,3000元以上就可能屬於數額較大。然而,在我們肉眼所見的世界,欺騙行為隨處可見,有人開美顏騙打賞,有人裝純情釣金龜婿,有人立虛假人設賺得盆滿缽滿。也許,人類社會和動物世界,一個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充滿著隨處隨時可見的爾虞我詐。但是,這些欺騙都構成犯罪嗎?顯然不是,刑法只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只有那些最為嚴重的欺騙取財行為才構成犯罪。那麽什麽叫做“最為嚴重的欺騙行為”呢?在理論界有很多種理論,但是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刑法學界的通說認為,詐騙罪一定是行為人的欺騙行為導致他人陷入認識錯誤,並基於認識錯誤處分了財物。張三說自己是秦始皇轉世,讓李女給他打錢,許諾李女將來可以飛黃騰達。李女信以為真,不僅給張三錢,還獻身侍奉張嬴政。顯然,李女因為張三的欺騙陷入了認識錯誤,張三構成詐騙罪。有人會說,這怎麽也會有人信啊?!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如果詐騙一般人構成詐騙,那麽詐騙傻子是不是更應該是詐騙罪呢?然而,對於此類案件而言,其背後最根本性的哲學爭議在於:民眾有沒有犯傻的權利呢?有人認為,為了保護民眾,應該不允許他犯傻,最大範圍地打擊欺騙,杜絕引發他犯傻的誘因。這個叫做家長主義,也就是以為你好之名,通過懲罰你的交易對象來限制你的自由。與家長主義針鋒相對的立場是自由主義,認為法律不能幹涉民眾犯傻的自由,因為吃一塹長一智,只有允許民眾有試錯的機會才能促進民眾的心智成長,否則民眾都會成為巨嬰。更何況,國家憑什麽認為那就叫做犯傻呢?比如燒紙錢。這最典型的就是20世紀初美國的禁酒令,為了防止民眾酗酒,幹脆認為賣酒一律構成犯罪。今天,很少有人認為法律應該禁酒,但是大多數人可能還是會認為禁毒還是有必要。自由主義和家長主義之間始終有一個模糊的平衡點。張三談了十次戀愛,被渣男騙了十次,張三非常生氣,覺得法律中完全應該規定一個“渣人罪”,一切不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都應該判刑。但是,如果戀愛沒有遇到渣渣的危險,因為法律規定戀愛必須結婚,兩次以上戀愛沒結婚者一律構成非法戀愛罪,五次以上屬於情節特別惡劣,最高可判處死刑。你真的想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嗎?我個人的粗淺認識是,對於“做法事”是否構成詐騙,可能還是要區分創造他人的認識錯誤與利用他人認識錯誤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在千年狐妖案、狗血消災案中,行為人創造了他人的認識錯誤,把他人徹底物化了。對這些行為認定為詐騙罪還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如果被害人本來就是有某種想法,行為人只是利用並強化了這種想法,這種對他人認識錯誤的利用導致財產損失就不宜以犯罪論處。比如張三有一匹250萬的名貴寶馬,現在馬生病了,張三找到獸醫李四,讓李四對馬實施安樂死,李四心裏笑開了花,因為李四很討厭張三的張揚,而且知道市面上其實有一種藥,馬吃了就會好,但是我為什麽要告訴你呢?所以對馬實施了安樂死。李四當然違反了職業道德,但是並不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因為張三的確授權李四對馬實施安樂死,雖然李四利用了張三的認識錯誤。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徹底理性的人,我們的交易行為簽署合同或多或少都有各種各樣的非理性沖動。如果僅僅因為人們不夠理性,所做出的同意不太完美,就導致一切交易行為被撤銷,那麽這種杜絕一切交易危險的社會遲早會崩潰。然而,人身損害不同於財產損害,如果利用他人認識錯誤實施了人身損害,比如張三在酒店走錯了房間,誤入李女房間,李女沒有開燈,以為自己的男朋友來了,張三將錯就錯,兩人發生了關系。這種利用他人認識錯誤的行為,還是應該以性侵犯罪論處。通俗說來,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失的法益侵犯性質不同,如果認為其屬於犯傻,那前者也許是犯大傻,後者則可能是犯小傻。如果利用他人犯傻來攫取利益,與犯小傻相比,對於犯大傻的禁止,理由應該更加充分。必須承認法律問題確實非常復雜,我時常覺得有心無力。為了尊重個人的自由,不要動輒把民眾當作長不大的孩子。如果做法事只是當地的普遍性民俗,民眾心理存在某種超越經驗的確信,不要動輒以封建迷信之名認為民眾在犯傻,更不應把沒有創造他人認識錯誤的人視為詐騙罪。對於國家權力而言,謙卑依然是必要的,我們必須對未知的領域保持足夠的敬畏。人類的有限性在於,我們對於罪與非罪的界限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這也是為什麽司法的專業判斷離不開民眾樸素道德情感的填補。專業人士必須承認自己的專業知識本來就存在大量盲區,對於人類千百年歷史形成的普遍性知識,專業人士更是知之甚少。在某種意義上,知道就意味著不知道,知道的越多,也就越多的不知道。不要動輒開啟全能全知的視野,讓自己成為充滿專業偏見的愚人。刑法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因此對於一種社會生活普遍許可的行為,無論如何它都不應該是犯罪。有一段話我引用過多次:“在任何情況下,立法都要適應一國當時的道德水準。如果社會沒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譴責某事,那麽你不可能對它進行懲罰,不然必會‘引起嚴重的虛偽和公憤’”。總之,對於道德生活所容忍的行為,發動懲罰權要慎之又慎。